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2):危难时刻十万铁军紧急驰援唐山

7月28日,是河北省唐山人民不想提起的日子,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哀悼纪念日。作为一个老兵和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每逢此日,我的心情便难以平静。
唐山地震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76年初春至初夏,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
7月,病重,已不能接见外宾。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年初,主持中央工作的被“打倒”,军委主要负责人“靠边”,“”为篡党夺权,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迫害各级领导干部。
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生多艰,民怨沸腾。恰在此时,自然界的灾害又骤然降临!
灾后我们才得知,地震发生前,我国地震工作者已在严密注视京、津、唐地区的震情,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包括“”对地震工作的干扰破坏,但主要的原因是科学技术问题),十分痛心地错失了通过中央,向有关地区打招呼的时机。
地震在凌晨3时42分发生后的一段时间时里,由于记录的地震仪打出了格,致使震中判断不明;直到早晨,唐山驻军发出的电报传到北京,8时,驾车前来的开滦煤矿工人李玉林等人和从唐山驾飞机前来的空军某部干部进入,直接向国务院报告灾情。
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向唐山派出救灾部队和其他救险队伍的决策,并紧急部署了全国的抗震救灾工作。
7月28日上午10时,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乘飞机抵达唐山。12时许,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肖寒乘坐的飞机降落。下午2时,的指挥机关到达。
我当时任副政委,于1976年7月29日中午到达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中央决定,指挥部总指挥为刘子厚,副总指挥有肖选进、万海峰、马力、马辉和我。
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我们进入唐山的时候,看到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好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遭受了袭击的广岛,铁轨扭曲,桥梁断裂,除了孤零零的几座建筑,民房几乎全部倒塌。
由于地震发生在凌晨,无数群众被砸死砸伤在废墟中,灰黄的尘雾弥漫天空,到处是令人心碎的断壁残垣。7月28日下午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紧接着大雨滂沱,地上的泥浆都被血水染红。
在20世纪人类所蒙受的自然灾害中,只有日本关东大地震(1923)、孟加拉风暴潮灾(1970)、非洲大饥荒(1968-1973)等的惨况可与唐山地震相比。
地震发生的瞬间,中国大地,北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至江苏省靖江市,西到内蒙古磴口市,东至鸭绿江边,有感范围达14个省(市)自治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在地震区铁路上开行的28列火车,有7列脱轨颠覆。全世界有的地震台监测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发生了8级以上的地震(我国核准为7.8级)。
唐山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占全国的1%。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开滦煤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包括冶金、发电、陶瓷制造。唐山地震,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的重要支柱遭到重创。
所有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都对唐山人民的坚强性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称唐山是“无泪的唐山”。当大难和悲剧突如其来时,唐山人民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以顽强的生命力自助自救,与灾难抗争。
地震后的一段时间里,唐山人民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白天烈日曝晒,苍蝇肆虐,夜晚无遮无盖,蚊虫叮咬,余震频频。
他们常常要排很久的队,领一些救济食品,领一桶从外地运来的清水。为了灾后的安全,为了越冬,我们多次要求他们迁移住处。
他们起初住的是芦席棚,后来少数人住过帐篷,再后来建造了以油毛毡为顶盖的简易越冬房。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中,他们含悲负重,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力。不仅在生活上挺过来,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工作,恢复生产。
震后第二天,某工厂的工人就用从废墟中扒出的手摇发电机发电,在一条尚未清理的小路上点燃了路灯,在心理上给唐山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慰藉。
印刷厂的工人从废墟中拣回大大小小残缺不全的铅字,为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印出了第一份通告。煤矿、钢铁、电力等系统的工人,也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开动了机器。
1976年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的伤员大转移。
截至8月25日,共计有159列(次)火车、470架(次)飞机,将10万多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上海。
各地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唐山,各地的救援队伍马不停蹄赶赴唐山,公路上挂着各省车牌的车辆穿梭往返,机场上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品……那万众一心、共赴危难的感人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包括、、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基建工程兵和各军(兵)种、大军区所属医院的十万名指战员参加了唐山抗震救灾。
除震区内驻军外,最早进入唐山灾区的救援部队,是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某部一营。
他们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进入唐山市区,与此同时,和的两个野战军也已奉命紧急出动,从唐山的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向唐山实施摩托化开进。
地震毁坏了桥梁,两个军下午分别被阻遏在蓟运河和滦河边,在十万火急的当口,一支部队利用机耕小道迂回,一支部队冒着危险,从摇晃着的铁路桥上强行驱车通过。
某部二营7月28日上午正在实弹射击,接到命令,未吃午饭就立刻出发。当他们翻山越岭,泅水渡河,步行赶到唐山市区的时候,已是次日清晨。
炊事班架锅熬出了一锅米粥,战士们刚端起茶缸站起身子,又不约而同地坐下了,他们看见大锅旁站着饥饿的唐山孩子们。
就这样,第一锅粥分给了孩子们,第二锅粥分给了路边的群众,第三锅还没熟,他们就接到了救人的命令,上了废墟。
当时的情形较为混乱,我们在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失误,没有让开进的部队携带大型施工机械,连锹、锤、钎、镐带得也很少。
最初的5天里,战士们硬是靠双手和就地找到的简易工具扒碎石,掀楼板,扯钢筋。
28日下午,最先进入唐山的某营,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指甲剥落,双手血肉模糊。在没有作业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把原有3层楼高的新华旅馆的废墟翻了个遍,救出了70多个幸存者。
随着时间推移,废墟中的幸存者慢慢的变少,部队成立了许多“潜听队”,每晚到废墟上屏息静听地下的动静。一有动静,立刻紧急出动,奋力挖掘。
到8月13日,部队从废墟救出群众12245人。与此同时,严防瘟疫是我们指挥部工作的重心。
人们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事实上,灾后唐山的疫情的确十分严重,各种传染病的发病苗头不断出现。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和军用防化车、喷药飞机、大批药品器械投入防疫工作。
部队担负的最主要的工作是掩埋尸体。这是一项繁重而又险恶的工作,参加掩埋的战士极易中毒。
且不说防护用具不可能应有尽有,即使有,战士们又怎忍心在失去了亲人的唐山人面前,把自己这样那样地保护起来?
掩埋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得知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战士开始生毒疮,许多年轻战士的疮口淌着黄水。
战士们夜以继日地做这种高强度的特殊劳动,有的战士疲倦至极,夜晚就在尸体堆旁睡着了。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唐山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爆发期。第二年春天,传染病发病率比常年还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唐山的大批孤儿在转送到外地之前,大都被收养在部队的营地。有的连队,平均三个战士照看一个孩子。
在执行任务的军车驾驶室里,时常能看到随车的孤儿们,他们身裹着军大衣,手里拿着苹果,捧着小人书。
可亲可敬的,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孤儿后来参了军、提了干,成为光荣的人民战士。
十万大军的行动是无声的昭示,它告诉灾区群众,当年老红军、老八路热爱人民、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如薪尽火传,代代常新。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唐山机场,飞机一天最多时起落354架次;空军指战员用塔台车指挥飞机双向起飞,调度员用目测和经验,指挥了数千架次飞机的安全起落,在危难时刻铺平了救死扶伤的空中通道。
铁道兵战士顽强奋战,仅用10天时间,就使京山线恢复通车。即使在混乱的废墟上,救灾部队依然纪律严明,军容齐整,绿色的军用帐篷排列有序,四周是宽窄一致的排水沟,让人想起古战场上的威武营帐。
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尤其需要唐山抗震中那种军民一心、军政一致、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的高昂士气。唐山抗震救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刻的经验教训。历经磨难,从废墟上挺起脊梁的中华儿女,是任何困难险阻都不可折服的。撼山易,撼我军民难!
7月28日,每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薛建国都要烧几张冥钞,给早逝的亲人,还一个铭心刻骨的愿……
燃烧着的冥钞随风悠悠地飞升着、舞蹈着,他的眼圈便红了。这个也曾当过兵、坐过机关、下过海的小老板,人近中年时,还的是一个城市的愿……
40多年前的那个灾难日,15岁的薛建国睁开眼睛时,看到阴霾的天空,偶尔有一两颗星星在头顶闪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睡在三层的楼上家里,怎么到了外面?
在很静的一刻过后,城市像突然惊醒似的,发出了哭喊声。他听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呼救,声音像是来自地下。
高大的楼房倒塌成一片废墟,水泥的预制板成为生命的障碍,他还稚嫩的双手,实在撑不起那生命的希望时,他看到了亲人的身影。
一年后,将军曾在他的文章里,记录了最先进入灾区的部队某营,时间是7月28日当天的下午。但事实上,人民子弟兵的援救和牺牲,都比将军所说的早得多。
薛建国一家住在某部的留守处大院,6栋住宅前是警卫连的四层楼房,那里有90多名某部防化连的官兵。大院也在这次灾难中最先感受到亲人的帮助。
薛建国是立即向那些赶来的战士求救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还在废墟里。在战士们动手清理废墟时,他又看到了几名战士正在周围扒人。
那时,天刚蒙蒙亮。也许是一种自然的依托,他至今还记得四周的那些战士有二三十个,后来他才听说,那几乎就是警卫连走出这座城市的全部人员。
在第三个邻居被救出废墟后,薛建国的母亲才从砖石里露出脸来。她的下肢被水管卡住了,水管又被水泥板压住,十几个战士齐心合力,才将母亲救出来,那时,已到中午了。
7月28日午时,落起了小雨,母亲被抬进院里惟一的一处帐篷。帐篷一边搭在一辆卡车车厢上,一边斜拖在地上,像山西人的半坡房。
这里曾是篮球场,平坦一些,被救出受重伤的战士也一个个被抬过来,但他们都没有抬进帐篷,帐篷挤不下,他们也不愿进去,就在雨中淋着。
后来,不知谁弄来一些塑料布,人们就用木棍支起些三角架来,挡在了战士身上。雨停时,太阳就冒了出来,天又热得难耐。
现在想起,那些伤员一定很需要更加多的帮助,可大家都在忙,忙得许多该做的都没能做。
傍晚的时候,掀开塑料布,有的战士已牺牲了。那时,人们才知道,前楼的警卫连伤亡惨重。
但因为几乎每家都有人震亡,大家的感情有些麻木了,谁也没有询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名字,也没有人问起抢险战士的名字,甚至那时天天见面,却不知道谁是恩人。
“其实,我们是能做到更好一些的。”薛建国讲完他的故事后,低低地说。几天后,他一家都随部队去了外地。
我和他很熟的时候,他才给我讲了这个埋在心里的故事,那天,我说起在他那张很男子汉的微黑的脸上,怎么有一双同样黑亮,却隐含一丝忧郁的眼睛时,他断断续续对我讲起他的故事,然后问我,那时,他为什么只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他是否太自私了?
那以后,我也有意了解那个大院里的人们,一直在军营的白兴明所长,是震前离开唐山,去了承德的,地震后又回了唐山。
他告诉我,当年防化连的损失的确很惨重,既要自救,又要救人,多数战士都牺牲了。都是五湖四海赶来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几天后,当脱险的战士,凭着早已磨肿的双手和透支的体力,再也无力救助时,被深深埋在废墟中的战友遗体,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如今的干休所里,已找不到当年的老住户了。2005年秋天,这里重新进行了规划建设。
我是在市直机关,辗转找到一位曾经的住户的,他是我一个十几年的朋友,他叫程杰。
程杰是被尘土呛醒的,那年他14岁。水泥板幸运地在他的头顶搭起了个“窝棚”,他便顺路爬了出来。
他家住最后一排,战士们来得晚一点,但也都是上午的事。父亲和姐姐虽然都受了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母亲已遇难了。
也像当时大多数脱险的人们一样,程杰也相信自身住的这一片是灾情最重的,他当然也听说过别人的事,但他没有太留意,更没有详细打听什么。
他说,当时自己太小了。或者真是这样,我们都太小了,我们只知道是强者,强者能帮助别人,强者怎么能也需要人去帮助呢?
我曾查过一些资料,证实当年人民共救出被埋压群众1.64万人,而城市当年驻军的2万官兵中,遇难近千人。
这座城市曾将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而那些异乡的战士,我们却说不上一个名字。
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想对那些年轻的、如流星般滑过的生命表达一份敬意,都很想为那些遥远的,如今已统统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道一声珍重,这些日子,在我寻遍了我所能达到的领域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一个,逝者如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白所长摇着头说,近30年了,部队几经整编,原来那部队已没有了,就是上一级部队,也不可能再保留你想找的那些资料了。
我说,至少我还能找到他们的墓地吧,前几年,我曾到过唐山许多公开的墓地,寻找遇难军人的归宿,但我仅仅发现两处。那么多遇难的军人,该会有一大片的墓地吧?准确的位置又在哪儿呢?
白所长说,和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一样,战士们的遗体都自然安葬了,在那些埋葬遇难群众的地方,也许就有我们的战士,在那些墓地,没有人能分清哪是军人,哪是百姓,哪是本地人,哪是外地人。
只是,我们的那些战士,没有人去祭奠……不,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他每次祭奠亲人时,都没有忘了子弟兵……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我站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读着那镂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二十四万城镇和乡村居民殁于瓦砾……”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那以后,我曾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公开刊物,没有谁能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帮助过一个遇险战士……像我的那些朋友说的,可惜我们没救出一名战土,哪怕在他们负载很重的身上,撤下一片砖瓦。
当这座城市曾以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离唐,当这座城市曾一次又一次获得双拥模范城称号,我相信那情感的真挚,那真挚,是欢笑,也有泪水。
同样的,10万抗震救灾子弟兵撤离唐山的时候,是整整40多年前了。那个同样初冬的早晨,阳光仿佛出奇地刺眼,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往战士们怀里,塞去煮熟的鸡蛋和包好的水果。
40多年前的初冬,在由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记述百万唐山人送别这一动人场面的长篇通讯中,提到一段最令唐山人动情的情节:一名战士6次闯入废墟抢救遇险群众,第7次时,他牺牲了。
在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我见到了王彦修的遗像,那是年轻的如朝阳般的年龄。
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
这个家乡距邢台不足80公里的宁晋县的小伙子,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坍时,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
第二年4月,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但当我一步步接近那个残酷的谜底,我想我该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就像原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原市委领导张乾说的:“决不止一两个的,不止的!可惜那时,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每天都有人去世,即使听到有战士牺牲,也只是叹息几声,哪有工夫细问。”
是的,那是不容人回头的日子,可人们总该有回头的时候,当日子过去近30年时,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去做了。
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市民政局也有统计牺牲的烈士们的想法,但没有办成。
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烈士这一栏。
民政局扶贫办的郑印庆告诉我,当时援唐的10万大军中,下至营级,上至大军区的建制,共有100多个单位,而且这些年,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
即使地震10年后,部队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了:“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
但烈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郑印庆以当年亲身经历告诉我,老领导张乾的话是对的。
在冀东烈士陵园,我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我,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
我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了那座烈士墓。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惟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
墓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
那以后我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赵俊杰,市民政局、地震局、唐山军分区以及写过许多唐山地震作品的作家王立新,都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
韩峰告诉我,这墓也不知是何人建的,当时陵园的围墙都倒了,埋了许多人,后来都迁出去了,我们看是个,就没动。
他还告诉我,这是陵园里惟一的一座实墓,按国家规定,60年代后,便不许埋实墓了。但直到退休,他也没见过烈士的亲人祭奠过。我又问过卞江,他摇摇头,
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年9月9日立。
刘主任告诉我,红漆是红领巾们干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
刘主任是女,很年轻,一袭红衫。我们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直到她随手采下一株野菊花,放在墓碑上。
我蹲下身,凑近花束,花有一种淡淡的香,就连那些枯萎的花朵,缩成褐色的一团了,但香气依旧。
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我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
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有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某部侦察科长的离休干部曹大连,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天,部队的侦察排长叶如松带着几名战士,在如今的唐山百货大楼北一栋倒坍的楼房里救人。
3个小时后,人们把叶排长和一名姓张的新战士扒出来,叶排长的头被预制板夹扁了,早已牺牲,那姓张的新战士双腿粉碎性骨折。
至今,曹大连还记得一位当地的老大妈,跪在叶排长的遗体前,一面用手指抠他嘴里的土块,一面抚摸着他的头。
他才20岁呀!人们只知道他是衡水地区的人。曹大连说,仅在他所在的师直机关,在抢险中牺牲的军人就三四个,可惜后来部队被多次改编,恐怕记录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地震救援结束后,唐山百万居民送亲人。难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都淡去了吗?
那年的7月28日傍晚,一辆满载伤员的军用卡车从唐山驶向天津医院,当时同样是伤员的张伯兰老人坐在驾驶室里,司机就是从废墟中把他救出来的,人们叫他连长。
连长头上缠着纱布,血浸透了纱布,流过脸颊,染红上衣、裤子,他的嘴里一直自言自语“时间,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车到天津医院,连长的血已染红驾驶室的地面,他是被医生抬下去的,第二天,医生向打听连长情况的人,含泪摇头。
报记者、作家钱钢在自己的《唐山大地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
他是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20年后,上将在文章《撼山易,撼我军民难》中披露了当年从废墟中救出群众的数字:12245人。而多少子弟兵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军没有说。
就在我记下上面文字的时候,唐山的街头,寒衣节期间,为故去的亲人焚化的一堆堆纸灰,还没有散尽。
当我走过这些思念的时候,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初冬的夜晚,星光灿烂,我知道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故事,不论别人明白还是不知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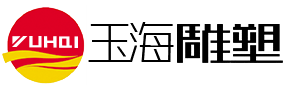

 相关推荐: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