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英雄讲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熟悉的乐章让人心潮澎湃。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我们大家一起探访烈士纪念馆,倾听英烈的故事,回首战火纷飞的岁月。
在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姚家庄村南侧,姚庆祥烈士的纪念馆就坐落于此。纪念馆正厅中央摆放着姚庆祥烈士的半身像,展板上写有烈士的生平事迹,还收录了社会各界人士写下的挽联。
记者在姚庆祥纪念馆见到了姚庆祥烈士的堂弟姚清卓,以及纪念馆管理员姚法诰。87岁的姚清卓和记者说:“我父亲兄弟3人,姚庆祥的父亲排行老大,我父亲排行老三。论起来,姚庆祥是我二堂哥,我比他小7岁。”
姚清卓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上面是他亲笔写下的姚庆祥英雄事迹:“原先是我父亲在馆里讲解,后来是我讲解。虽然讲了10多年了,但是在一些时间上,我担心讲不对,还是要看一看。”
通过姚清卓的讲述,记者大致了解了姚庆祥烈士的生平。“二堂哥是1929年2月19日出生的。我家住在村北侧的山上,二堂哥一家住在村南。小时候,我们两家都比较穷,他还给人放过牛。二堂哥从小干活就快,上坡割草时,别人的篓子还没装满,他已经割完了。他从小就喜欢交朋友,身边总围着一群小伙伴。村里一些当年和他一起玩的人回忆,他为人忠厚实诚。”姚清卓说,姚庆祥10岁那一年,他的父亲生病去世。12岁,他跟随母亲和兄嫂逃荒到东北。
姚法诰的父亲姚清升是原即墨二中的语文教师,曾经专门搜集过姚庆祥烈士的事迹,并撰写了一本《姚庆祥烈士传略》。书中描写了姚庆祥一家闯关东的经历:1941年春,姚庆祥一家到了吉林省和龙县,靠下煤井挖煤谋生。由于工钱太低,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1942年,他们又流浪到辽宁省阜新,还是靠挖煤为生。日本人的矿井都一样,活重钱少,难以糊口。1943年,一家人又到了抚顺。那时候,姚庆祥刚刚14岁。他跟着即墨老乡下煤井打棚子,干木工活。因为他个子小,干起活来格外费力,稍有怠慢,便会遭遇拳打脚踢。
姚清卓说,正是在煤窑里,二堂哥结识了一位员。这位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向大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听了这些,姚庆祥振奋不已,暗暗决心加入抗日队伍。

1945年7月的一天,姚庆祥回家告别母亲:“我要去当八路军,你不要找我。”就这样,16岁的姚庆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入了抗日队伍。8天后,他在连长的陪同下回家见了母亲一面,很快又走了。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
1950年10月,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已有5年军龄的姚庆祥主动写下请战书,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某侦察营。不久后,他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
在朝鲜战场上,姚庆祥始终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战斗间隙,他带领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被敌人毁坏的家园,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表现出色,他晋升为排长。
1951年7月,朝鲜战争停火谈判期间,姚庆祥调任朝鲜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排长,在板门店一带担任警戒巡逻任务,保卫着中立区和各方代表的安全。
姚庆祥率领的排共有3个班,分别驻扎板门店、松古洞和本松里。这一些地方都是谈判双方联络官在会议上确定的中立区,他们就在这个范围内担任警戒。
1951年8月18日傍晚,天空中雷电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越是这样恶劣的天气,越是要防止敌人搞破坏,姚庆祥带领一个班,冒着大雨,一路向板门店方向巡逻。他告诉战士们:“这几天情况更紧张了,敌人想寻找借口破坏停战谈判,上级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
当天半夜,姚庆祥从板门店到高头山向连里汇报工作,而就在这时,美军派出30多名武装人员,违反谈判协议,偷偷侵入中立区,由板门店的东南面潜入白鹤洞附近的山岗下隐藏起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伺机杀害志愿军战士,借以制造事端。
次日天快亮时,姚庆祥带领几名战士从连部出来,准备返回松古洞。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过他们身边。姚庆祥急速带人向枪响的地方包抄过去,同时嘱咐战士们:“这是中立区,不能随便开枪。要打的话,要等敌人进入腹心地区,并要活捉敌人,让敌人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否则,敌人会造谣、找借口。”接着,他命令九班长控制住右边高地,防止敌人从右边迂回。这时,战士王仁元高喊:“排长,右边高地树下有敌人!”王仁元的喊声未落,左边射来密集的子弹,姚庆祥中弹倒在斜坡上,王仁元也负了伤。
一名战士急忙跑到姚庆祥身边,想把他扶起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快去通知部队。”他命令九班长立即去和副排长带领的巡逻组会合。九班长走后,敌人向姚庆祥围上来。姚庆祥顽强地站起来,与敌人展开搏斗。他摔倒了一个敌人,自己也倒下了。这时,连长、指导员带着巡逻组赶来了。敌特队长金昌植见势不妙,向姚庆祥的头部连开两枪,抢走了他的手枪、衣帽和鞋子,慌忙逃窜。
因姚庆祥的大哥、母亲已相继去世,1951年9月,他的叔叔姚国球作为烈属,收到了姚庆祥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这份证明由姚清卓一直保存至今。
“家里人得知我二堂哥在朝鲜牺牲的消息后,都很难过。我父亲好长时间吃不下饭。我二堂哥到东北闯荡后,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家里太穷了,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姚清卓回忆往昔,脸上满是悲痛。
1951年10月25日,即东县人民政府在姚家庄召开万人大会,追悼姚庆祥烈士。“追悼大会就在我们村东北边的河套上举行的,我父母作为烈属参加了大会。那一天,他们哭得嗓子都哑了。”姚清卓说。会后,不少青年受到姚庆祥英雄事迹的感染,报名参军。18岁的姚法学就是这里面一员,参军后成为一名通信兵,跟随部队赴朝作战。村民姚法迪在1970年入伍,他以英雄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1975年退役回乡后,兢兢业业为村民服务了25年。当时,姚家庄共有10户军烈属。姚庆祥牺牲后,全村人重新修订了爱国公约和帮扶军烈属务工合同,通过换工、帮工、代耕、互助,保证军烈属的耕地不误收种、不减产量。
“当听说要修建姚庆祥烈士纪念祠时,村民们主动拆了5间民房、村集体学校,还拆了一座老祠堂和村委7间办公室,将原本只有一米半的路拓宽到10米。村所属的合作社改名为姚庆祥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学校。”姚清卓说。
1980年,青岛市政府对纪念祠进行扩建,更名为“姚庆祥烈士纪念馆”。1997年8月18日,姚庆祥烈士雕像落成。
战士无畏,他冒着炮火救治伤员;医者仁心,他常常边救人边红了眼眶。两次负伤被送回国休养后,他又主动请缨重回朝鲜战场。他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地医生赵引群。“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救治过70多名伤员。”回忆起在朝鲜战场上的日日夜夜,赵引群难过地说,没有来得及抢救下更多的战友,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1932年2月,赵引群出生于山西夏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党员,年纪轻轻就因反动派的迫害而牺牲,当时赵引群暗自立下志向:“一定要加入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赵引群和记者说,自己的学医之路从十二三岁开始,当时他给一个日本医生做服务生。“早上帮他打一下洗脸水,晚上打洗脚水,中午把暖瓶装满开水,其余时间我都很闲。这位医生忙得很,我闲着没事,就专心致志地看他给人治病换药。后来他注意到我对治病很感兴趣,就问我‘愿意学医吗?’我兴奋地回答‘当然愿意’。他就开始一点一点地教我。后来这位日本医生回国了,另一位中国医生接替了他的工作,我的学徒生涯却持续了下来。”
15岁那年,赵引群参军入伍,加入夏县独立营。解放战争时期,他被编入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担任卫生员。因为医术精湛,赵引群18岁就当上了副班长。方圆几里的百姓都对他的医术有所耳闻。
太原战役时,赵引群接收了一名受重伤的班长。伤员大腿动脉出血,压住伤口止血的衣物已经完全被浸透了。说起当时的经历,赵引群颇为自豪:“我当机立断,用止血钳‘啪’地夹住伤口,伤员的血喷了我一手,但总算止住了。我又连忙用线把伤口缝合起来。”后来,这位班长被送到著名的白求恩医院治疗,外科主任给他换药时,惊讶地问伤口是谁处理的。得知是一个小卫生员后,这位资深的医生连说“不可能”,并详细询问了当天的情况。听后,那名医生感叹,好多从业多年的大夫都没有这种止血技术,你应该感谢这个卫生员一辈子,你的命是他保住的。
“抗美援朝的号召发出后,有部队来招募医术好的医生,去战场上救治伤员。许多人推荐了我。”赵引群和记者说,他就这样踏上了去朝鲜的征途。到了战场上,他作为医疗小组的一员,辗转各个战场,救治最危重的伤员。
“战场上炮火纷飞,志愿军伤亡惨重。救治伤员最重要的是一个‘快’字。要快一点、再快一点,才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我们瞅准时机迅速把战壕里的伤员拉回来,止血钳‘啪’地一夹,再上药,三下五下包扎好,动作必须麻利。”赵引群说,自己不愿多回想战场上的场景,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牺牲。“有时候敌人的炮火太密集,我们根本没办法出去把伤员救回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牺牲,那种心痛无法描述……”赵引群擦了擦眼泪,“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救治了70多位伤员。”
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赵引群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战场上,全力救助伤员。“我在战场上主要负责救治重伤员,处理最危急的情况。经常听到有人大声呼喊:‘赵大夫,快到这边来,这个人要不行了!’我就拼了命地跑过去。救治重伤员后,我会在他的手腕上系一条红布条,表明此人重伤。布条共有红、黄、黑、白4种颜色,表示不同程度的伤情。”
在一次救助伤员时,赵引群的左颈部被子弹擦过,血流不止。大家看着不断淌出的鲜血犯了难,伤口位置特殊,没有人能应付得来。最会止血的医生正是赵引群,而他无法自救。“很快我就因为失血过多休克,昏迷了过去。等我再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我问旁边的病友这是哪里,病友说是齐齐哈尔。我大吃一惊,自己居然回国了。”赵引群说。
这次受伤,让赵引群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我还记得昏迷的那一天,我的衣服上别着朝鲜颁发给我的军功章。醒来后却找不到了,估计是转移时弄丢了,我遗憾了好久。”这并不是赵引群第一次负伤。他第一次受的是轻伤,只休息了几天就回到了岗位上。这次,把身体养好后,赵引群又主动请缨,回到了朝鲜战场。“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赵引群这样对自己说。
回到朝鲜后,战争进入谈判阶段。仗打得少了,但仍有很多伤员需要救治,赵引群依然发挥着精湛的医术,在伤员间穿梭,忙得脚不沾地。“负伤再加上劳累过度和严重冻伤,造成我两条胳膊永久性损伤,现在怎么也伸不直了。”赵引群向记者展示伸直后仍带着弧度的胳膊。
战场带给赵引群的除了回忆,还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别看我那时年纪小,打仗可一点都不怕!”赵引群讲起了1948年晋中战役时遭遇的一次突围战。“部队得到情报,敌军要从我们后方医院经过,有近百名伤员来不及转移。政委下令找一个人担负起保护伤员的任务,我自告奋勇站了出来,并在短时间内制定了作战计划。我们把机枪、手榴弹集中放在门口,我主攻,两个战友辅助。”
十几分钟后,敌军来了,冲在最前面的是骑兵。赵引群灵机一动:“先打他们的马。马倒下了,人也跑不了!”随后是骑着摩托的敌兵,他随即改变策略:“瞄准人!打死了敌人,车咱还能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有伤员毫发未损,赵引群因此荣立一等功,并在战斗后光荣入党。
赵引群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太原战役、西宁战役等诸多战役。新中国成立之初,赵引群还参加了多次剿匪战斗。他不仅救治受伤的战友,还经常为当地群众看病疗伤、扶贫济困。
有一次在贵州某镇,一名苗族妇女因感冒发起了高烧。“她带着3个孩子住在两间破草屋里。治好了她的感冒后,我和连部几个战士上山找来稻草和木头,又凑了一点钱,用两天的时间帮她修好了房子。那个苗族妇女不会说汉语,我们走的时候,她跪下为我们送行,我们走出去百米远,她还没有起来。”赵引群回忆。
1953年,青岛组建海军潜水艇学校,赵引群被组织派到青岛,担任潜水医生。1965年他被调到北海舰队门诊保健科工作,担任眼科、牙科负责人。赵引群离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回忆录《战火纷飞的岁月》。
“我觉得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些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回来的战士们才是英雄。每每想到他们的尸骨未能落叶归根,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时,我无比激动。祖国从未忘记守护她的战士们,让我想起那首《祖国不会忘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赵引群眼含热泪,动情地唱了起来……
“目睹皆春色,清明佳节临。流落无定处,意中思故亲。”这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张所温在日记本中写下的一首诗。张所温与堂哥张所聘一同参军,又一起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令人痛惜的是,张所聘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上,而张所温右脚落下了残疾。近日,青岛市南区居民张士鹏讲述了父亲张所温和伯父张所聘的故事。

“我父亲出生于1931年,1949年和伯父一起参军。兄弟二人参加了青岛的马山、铁骑山、丹山战役。”张所温的大儿子张士鹏注视着父亲的遗像,陷入了回忆,“父亲接到集结赴朝作战的命令时,正跟随部队在南方驻扎。部队迅速赶赴集合地山东兖州。当时虽值深秋,但南方的天气十分暖和,大家都穿着短袖或单衣。来到山东后,当地的气温让衣着单薄的战士们很不适应。当时条件十分艰苦,部队下发的棉衣仅够三分之一的战士穿。许多战士就这么硬挺着,进入了朝鲜。”彼时的朝鲜长津湖地区户外气温已降至零下40摄氏度。
70岁的张士鹏唏嘘不已,父亲经常讲起,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队伍常常要在雪地里匍匐,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有些战士再也没能站起来。
“进入朝鲜后,父亲和伯父分别担任兵团的电话员和报务员,在战火纷飞中相互扶持。”张士鹏说道。1950年11月至12月,长津湖战役爆发。志愿军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全歼美步兵第七师下属三十一团,也就是著名的“北极熊团”。为了这场胜利,无数志愿军战士牺牲于异国他乡,其中就包括张士鹏的伯父张所聘。
张士鹏说,“据父亲讲述,1950年12月16日那天,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伯父被炮弹弹片击中腹部而牺牲。”张所温常常提起堂兄在自己身边去世的一幕。“父亲说,伯父躺在那里,鲜血直流,肚子被美军的炮弹炸出一个洞,内脏流了出来。父亲不忍心看,脱下衣服盖在伯父身上。当时炮火纷飞,他无法将伯父的尸体带走,只能忍痛撤离。”张士鹏和记者说,父亲回忆当年的场景时说,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只是跟着战友们奔跑。从那以后,这一幕就时时出现在父亲的脑海甚至梦里。还有什么比亲人在自己身旁牺牲更令人悲痛的呢?说到这里,张士鹏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张所聘牺牲3天后,张所温也负了伤,右脚脚趾全部被炸掉,失去了战斗能力,最终被评定为三等甲级残疾,在1951年初回国疗养。
“父亲是电话员,在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我们的无线电步话机比较落后,经常会出现信号中断的情况,使用有线电话更为可靠。作为电话员,首先要贴身携带电话线,以保证前方战报及时送达。每到一个地点,电话员要率先架线,过一会又要收线。有时信号不好,还要反复试线。电线公里路,收了电话线后要立马跟上部队。美军不分白天黑夜地炮击,电话线经常被炸断,每次电话员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接线。可以说战场上传递的每条信息都是电话员用生命换来的。父亲就是在接线过程中被炸伤了右脚。”张士鹏告诉记者。
1951年1月,张所温回到东北军区第二十六陆军医院休养,在此期间,他荣立二等功。
“我的妹妹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从一个铁皮箱子里找到了这本军功证。”张士鹏向记者展示了一本立功证明书,上面写着“劳动好,在休养中帮助护理员打水打饭;学习好,除自己学习外,还耐心帮助别人学习,每天报纸来了,读报给大家听;经常写稿子,表扬好的护理员,使战士们的情绪高涨起来。”正是这些细小却温暖的事情,让张所温成为大家喜爱和尊敬的人。
“疗养结束后,父亲开始重新学习文化知识,几年后又专心钻研专业方面技术。那些年里,父亲从未停止过写日记。”张士鹏搬出了20多本日记本,并告知记者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搬家,好多日记本还留在原来的房子里。
日记多为1952年至1979年间所写,字迹苍劲有力,颇有风骨。翻阅这些日记,记者看出,张所温善于思考、勤勉自持,有旺盛的求知欲,同时感情丰富细腻。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每天的所思所想,学习、科研过程和对自己内心的反观。他很擅于提问和总结,深入探讨了许多问题。日记中还有不少短诗,表达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心情与心境。光是这些日记,加起来已写了几十万字。“我们从始至终妥善保存着这些日记本,时不时地拿出来翻阅。每读一遍,我们对父亲的尊敬就多上一分。战争使父亲的思想一次次升华,这些高尚的思想也激励着我们兄妹3人,积极乐观地生活。”张士鹏说。
“乐于助人是父亲最明显的品质。因为在部队掌握了扎实的通信知识和专业方面技术,父亲精通于修理各种电器,尤其是电视机、收音机等。村里谁家的电器坏了,父亲都会上门帮忙修理。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富裕,要换掉零件时,他从不要人家去买,都是自己帮忙找来换上。有些少见的配件,他辗转托人买来,送到邻居家时却只字不提购买的艰难和花费的金额。要知道,他平时在生活中极度节俭。”张士鹏把这一些细节都记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成为和父亲一样心中有爱的人。“这些精神财富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张士鹏说。
张所温于2004年病逝,而张士鹏的伯父张所聘离家参军后便与家人断了联系。张所聘的女儿于1949年9月出生,名叫张玉秋。张玉秋从没见过父亲,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父亲长什么样。2021年3月,张士鹏和妹妹张玉英在网上偶然看到山东省公安厅退休警官林宇辉参加了为烈士画像的公益活动,于是向林宇辉求助。林宇辉将画好的画像拿给张玉秋看,70多岁的张玉秋怀抱父亲的画像哭了起来。张士鹏说,将来有机会,他们会和堂姐张玉秋一起到长津湖战役的战场上,看看大伯张所聘,为他扫墓。
“这好像是一个炒面袋。记得父亲说过,抗美援朝期间每个战士都带着后方老百姓做的炒面,有的还会装在长袋子中,背在身上。你看这个布兜,一面绣了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另一面绣了彩色的‘抗美援朝’4个字,落款为‘冯氏赠’或‘冯化赠’。这是父亲从朝鲜归来时,热情的群众赠送的,意义非凡。我们只记得父亲说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送的,再无别的信息了。”张士鹏说,希望能够通过青岛早报找到这个布兜的赠送者:“我们很想跟他(她)见上一面,聊聊当时欢迎战士们回国的情景。”
姚庆祥(1927—1951),又名姚清祥,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镇姚家庄人。15岁时,随母及兄嫂去东北吉林省谋生。1945年7月参加人民军队,1948年5月加入中国。1950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第四十七军一三九师侦察营,入朝作战。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姚庆祥奉命担任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排排长。8月18日夜间,在带领战士执行巡逻任务时,遭到潜伏的敌军袭击,壮烈牺牲。
赵引群(1932—),山西省夏县人。曾参加临汾、晋中、太原、临夏、西宁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一等功。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及抗美援朝纪念章等。
张所温(1931—2004),山东省潍坊市人。1949年与堂兄张所聘一同参军,参加了青岛的马山、铁骑山、丹山等战役。1950年两人同时入朝作战,担任二十七军九十四师二八〇团电话员和报务员,张所聘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张所温为三等甲级残疾军人,荣立二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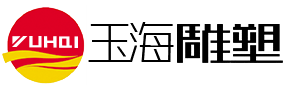

 相关推荐:
相关推荐:

